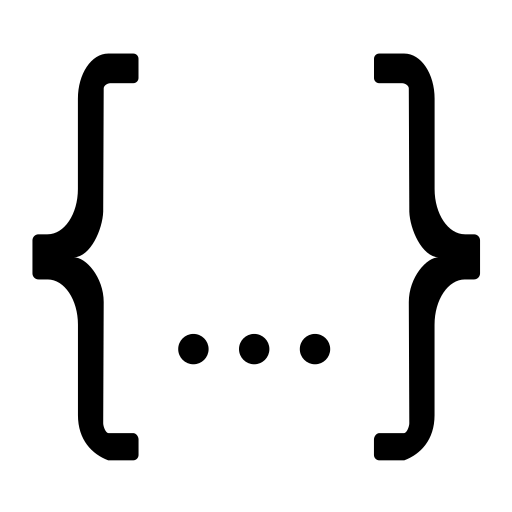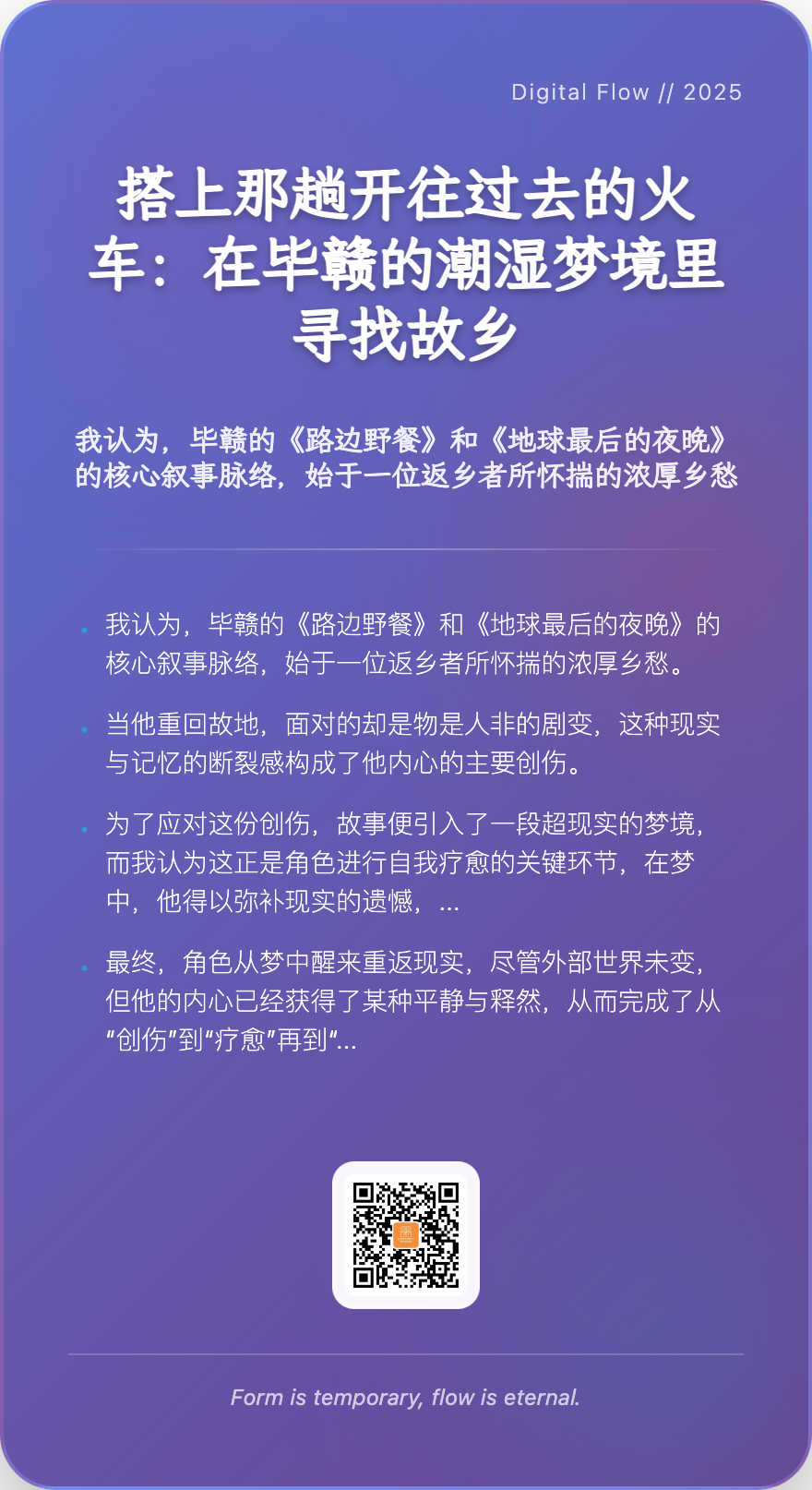搭上那趟开往过去的火车:在毕赣的潮湿梦境里寻找故乡
About
我认为,毕赣的《路边野餐》和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核心叙事脉络,始于一位返乡者所怀揣的浓厚乡愁。当他重回故地,面对的却是物是人非的剧变,这种现实与记忆的断裂感构成了他内心的主要创伤。为了应对这份创伤,故事便引入了一段超现实的梦境,而我认为这正是角色进行自我疗愈的关键环节,在梦中,他得以弥补现实的遗憾,与过往和解。最终,角色从梦中醒来重返现实,尽管外部世界未变,但他的内心已经获得了某种平静与释然,从而完成了从“创伤”到“疗愈”再到“回归”的完整情感闭环。
1. 浓浓的乡愁:返乡者的视角
这正是毕赣电影的出发点。他的故事总是围绕着一个“返乡者”展开。
- 在《路边野餐》中,陈升从诊所的日常中“出走”,踏上寻找侄子卫卫的旅程,这趟旅程实际上是一次回到过去、回到记忆深处的精神返乡。
- 在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中,罗紘武因父亲去世而回到凯里,这个物理上的返乡,开启了他对过去情人万绮雯和死去好友白猫的记忆追寻。
你感受到的“乡愁”,不仅仅是对故乡山水(凯里潮湿、迷离的亚热带环境)的眷恋,更是一种\\“时间的乡愁”\\。主角们怀念的,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特定时间点,是那个时间点里特定的人和关系。
2. 物是人非:翻天覆地的变化
你的观察非常敏锐。主角回到故地,发现一切都变了,但这种变化并非戏剧性的爆炸或冲突,而是不动声色的、充满失落感的\\“错位”\\。
- 物理空间的变化:也许是老房子被拆了,旧街道变了样。在《地球》中,罗紘武寻找的很多地方都已不复存在。
- 人际关系的变化:陈升的弟弟对他充满不信任,老医生疯疯癫-癫;罗紘武的母亲早已离开,童年伙伴也已死去。
- 记忆与现实的断裂:主角脑海中鲜活的记忆,与眼前冰冷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。他想找的人,要么不在了,要么变成了另一个模样。这种“物是人非”是驱动主角进入下一个阶段——梦境——的核心动力。
3. 梦境的疗愈:在时间的褶皱里与过去和解
这是你分析中最精彩的部分——“进入一段莫名其妙的梦境中治疗他的创伤”。这正是毕赣最具标志性的手法。当现实无法给出答案,当失落感达到顶峰时,电影便会用一个惊人的长镜头,将主角带入一个如梦似幻的场域。
- 《路边野餐》的荡麦:陈升坐着摩托车、轮船,走过那段40分钟的长镜头,在荡麦这个地方,他遇到了长大后的卫卫、像他妻子的理发店老板娘。在这里,时间是错乱的,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交织在一起。他完成了对侄子的嘱托,听到了爱人的歌声,实现了现实中无法完成的“团聚”和“告别”。这确实是一种精神疗愈。
- 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3D长镜头:罗紘武戴上3D眼镜,进入到一个废弃的矿洞电影院,然后在一个长达一小时的梦境中,他“找到”了万绮雯(或者说一个长得像她的女人凯珍),和她一起唱歌、打球、飞行。他念出了那段著名的咒语,让房子旋转起来。这个梦,让他弥补了现实中未能完成的告别,填补了心中的遗憾。这同样是自我救赎与创伤抚慰。
你的用词“莫名其妙”也很传神,因为这种梦境并不遵循现实逻辑,它遵循的是情感和记忆的逻辑。
4. 回到现实:梦醒后的余味
梦终究会醒。在梦境中得到短暂慰藉后,主角还是要回到那个物是人非的现实中。
- 《路边野餐》的结尾,陈升把风车和照片交给了同行的人,让他带给卫卫,火车载着他继续前行,窗外是倒退的景象,象征着他对过去的告别。
- 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结尾,罗紘武在即将燃尽的烟花和亲吻中结束了梦境,回到了现实。他是否真的找到了答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完成了这场追寻。
梦境并没有魔法般地改变现实,但它改变了主角的内心。他带着这场梦赋予他的慰藉,继续面对生活。所以,电影最终讲述的还是现实的变化,以及这种变化在人心中留下的永恒印记。
总结
所以,这会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解读框架:
返乡(触发点) -> 感受现实的物是人非(失落与创伤) -> 进入梦境(精神疗愈与遗憾弥补) -> 回到现实(带着和解继续生活)
这个结构就是毕赣电影诗意叙事的核心。他用诗歌、潮湿的南方意象和惊人的长镜头,构建了一个专属于记忆和时间的迷宫,让角色和观众在其中体验失落、寻找、并最终获得一种忧伤但温暖的和解。